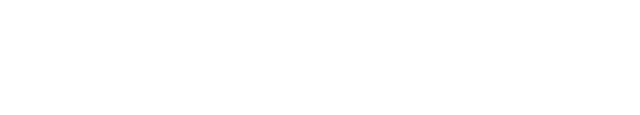

村上春树:极其“热门”的“冷门”


2019年10月10日,诺贝尔文学奖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如期公布,本次将一并颁发两个年度的文学奖。稍有些出人意料的,18年的文学奖颁发给了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19年的文学奖则归属奥地利剧作家彼得汉德克。同时亦在许多人预料之中的,常年稳居各大赔率榜,被国内许多人认为是诺奖热门选手的村上春树,再次名落孙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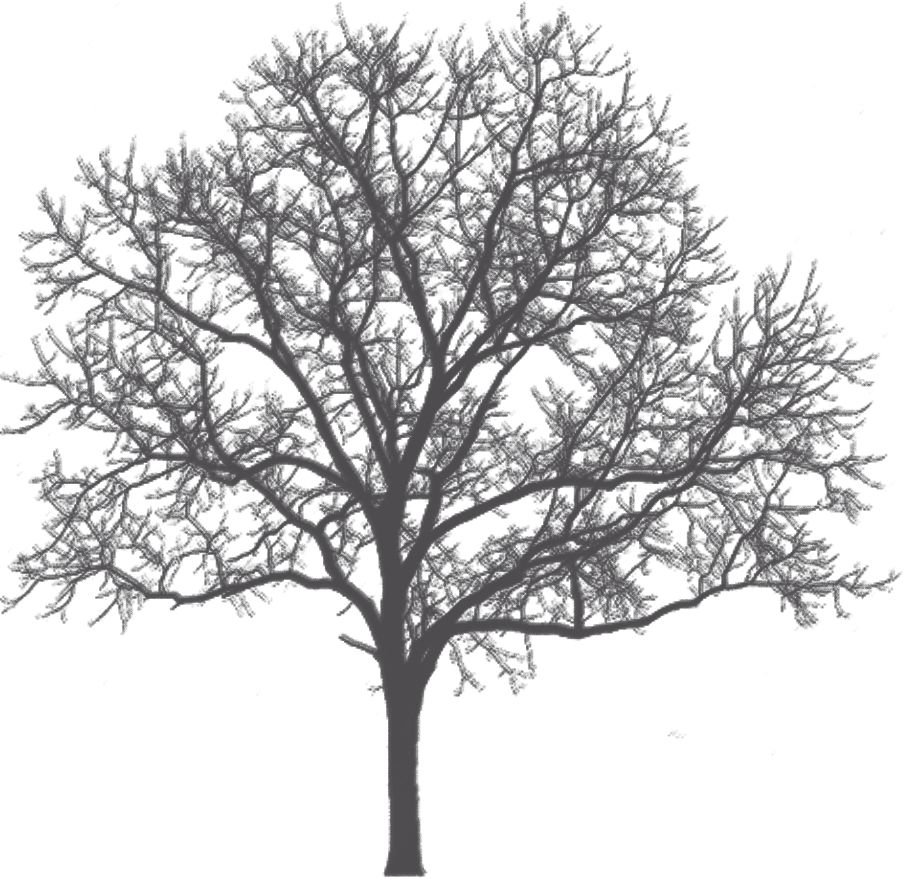

诺奖揭晓后,相信不少村上春树的书迷,或者是很多对文学略有兴趣以及接触过文学的人都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村上春树没有获奖?甚至有不少书迷调侃地称“村上已经陪跑了1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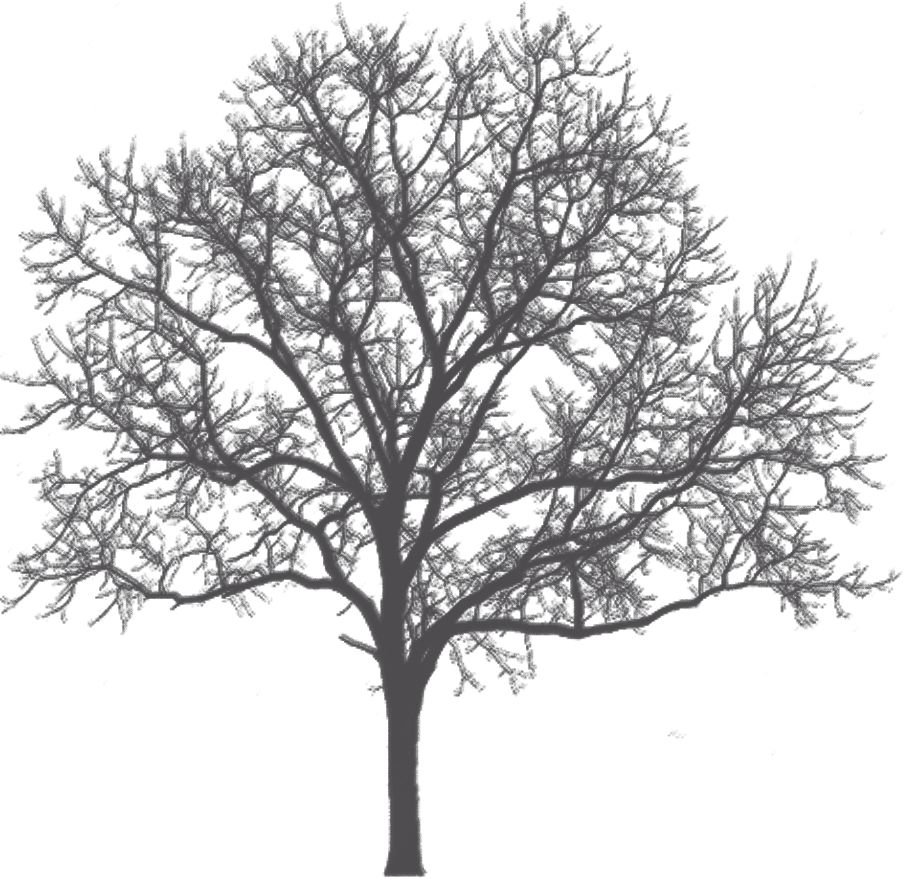

2006年村上春树获得了堪称是诺奖风向标的卡夫卡奖。当然,村上是否真的年年都得到了文学奖的提名,根据皇家科学院的保密原则, 50年后我们才能知晓。但自那以后,村上便是诺奖赔率榜的常客,并且身位居高不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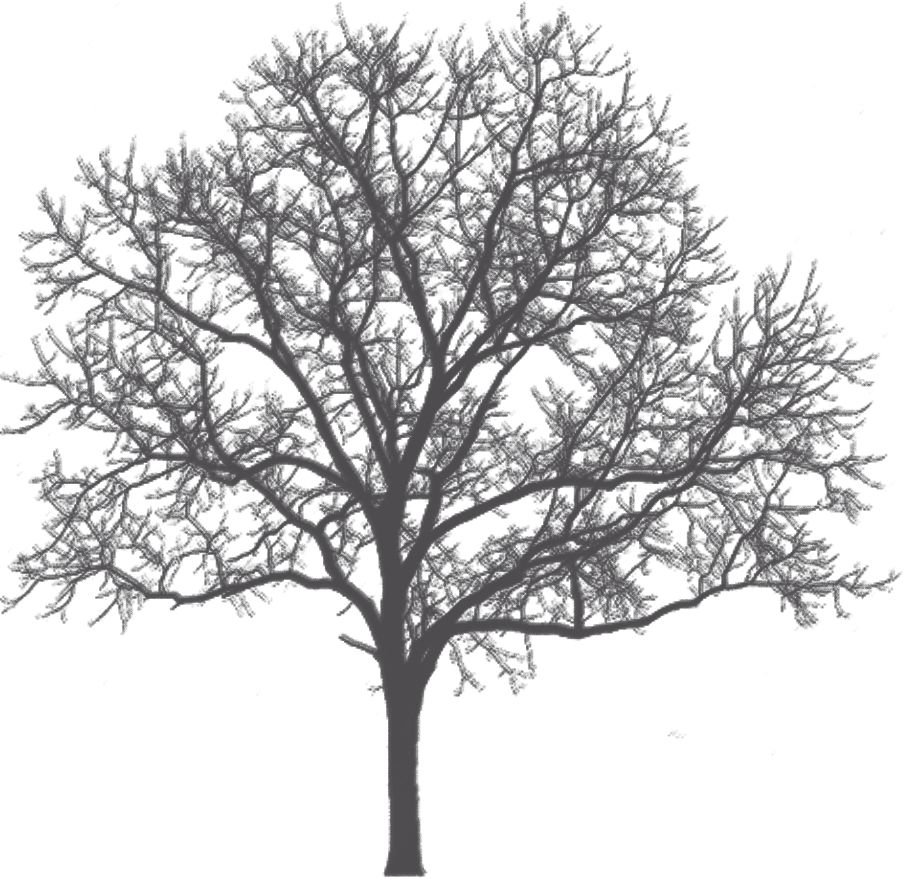

那么村上为何年年热门又年年无法加冕?
从文学奖历来的偏好入手,诺贝尔文学奖的审美标准是——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杰出文学作品,偏好“维护人的尊严与自由张扬人的价值和美好的作品”。“对人类价值的终极关怀,对人类缺陷的深深忧虑,对人类生活的苦苦探究”是多数获奖作家的共同点。由此观之,村上春树似乎有着天然的优势,毕竟无论是《挪威的森林》中对经济飞速发展的日本社会中,年轻一代人膨胀的物欲和失衡的价值观产生的一系列焦虑、孤独与迷茫的探寻,还是《1Q84》中通过诸多社会问题折射出对于世界和人类走向的担忧和思考,都踩上了诺奖的得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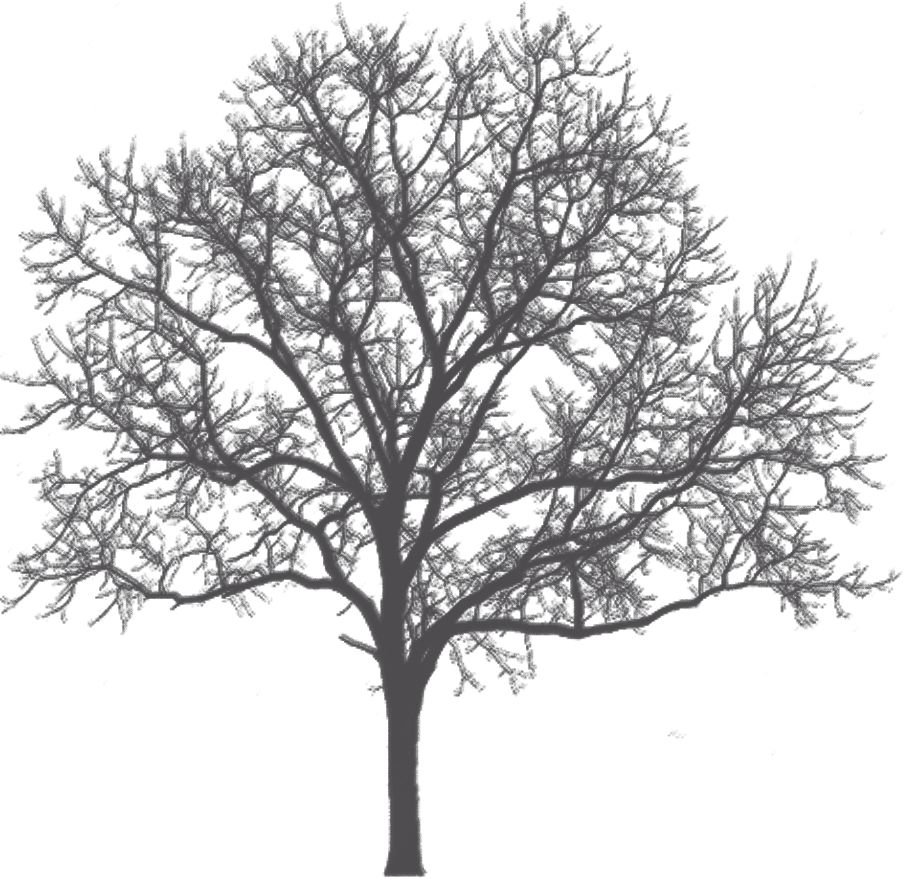

然而,最大的问题却恰恰是他都有,却未曾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村上更多的是在探寻内心世界,冲突并不激烈,以至于许多矛盾都是在沉默中趋于妥协。矛盾中心的女主角最接近爆发的行为也就只有抱着男主痛哭,悄无声息地死去。这种程度自然难以打动诺贝尔奖的评委,没有“决裂”,没有“爆发”,他们只会觉得村上的作品太过于“无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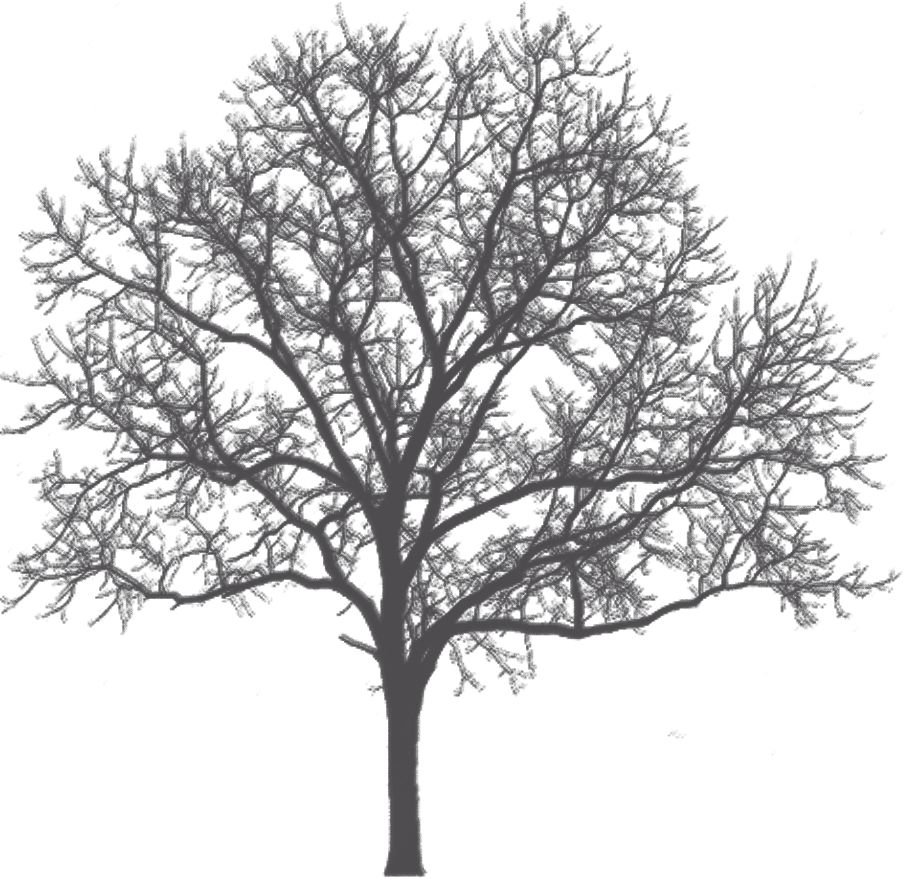

而且在村上的文学世界中,善恶之间并不存在无法跨越的鸿沟,村上甚至乐意去在善恶间架上一座桥,使其成为一个模糊的概念。比如在《1Q84》的邪教教主口中,就相应成为了这样的表达:“善恶不是静止的固定的,而是不断变换场所立场的东西,一个善在下一瞬间就可能转化为恶,反之亦然。”也正是因为如此,村上虽然体现了所谓的人文关怀,但在其作品中并没有理想主义的成分,对于现实社会的批判性远远谈不上深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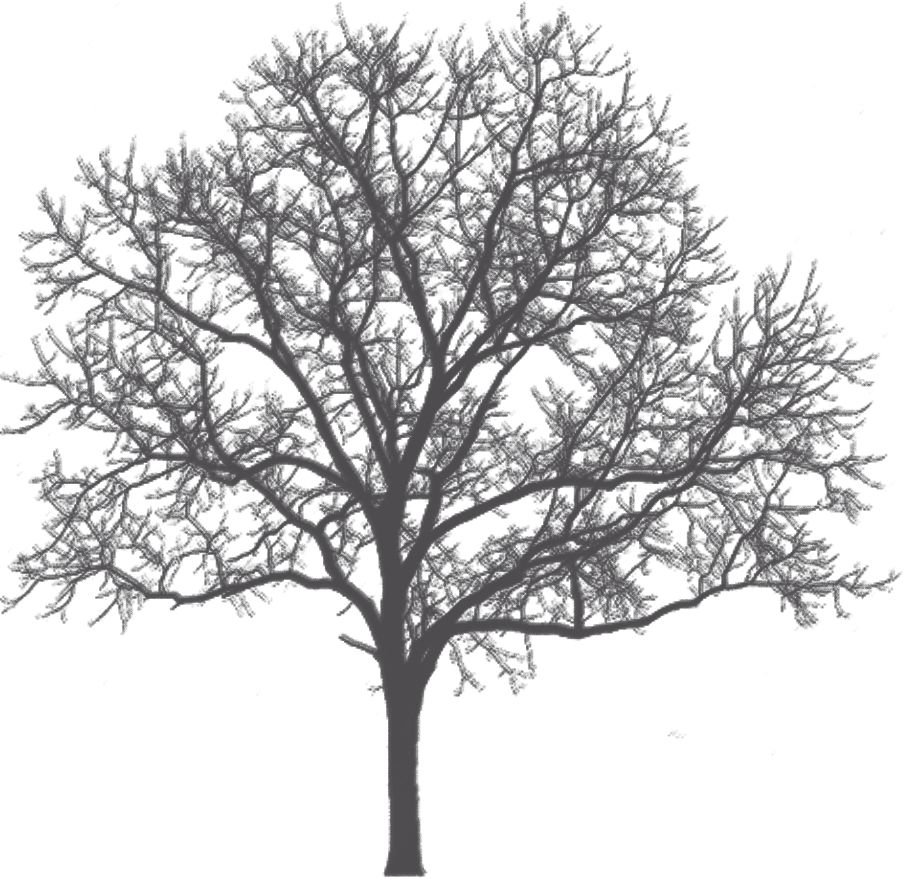

不过,理想主义只是诺奖评委的偏好之一。除了考虑作家的人文关怀及普世价值,文学奖也兼顾其本土性,也就是这位作家能否在一定程度代表他所属国家的文化沿革。而村上春树的作品却缺少这一元素。截止到2019年,有两位日本籍作家获得文学奖——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
川端康成推崇日本传统的幽玄之美,出现了大量的传统文化要素。哪怕故事发生在已然高度西化的东京,依然可以从樱花,和服等元素中一窥仅属于日本的风采。而大江健三郎,则通过诗意的想象力,创造出一个把现实与神话紧密凝缩在一起的想象世界,充满了东方神秘主义,很明显的体现出日本作为一个神道教色彩浓厚的国家的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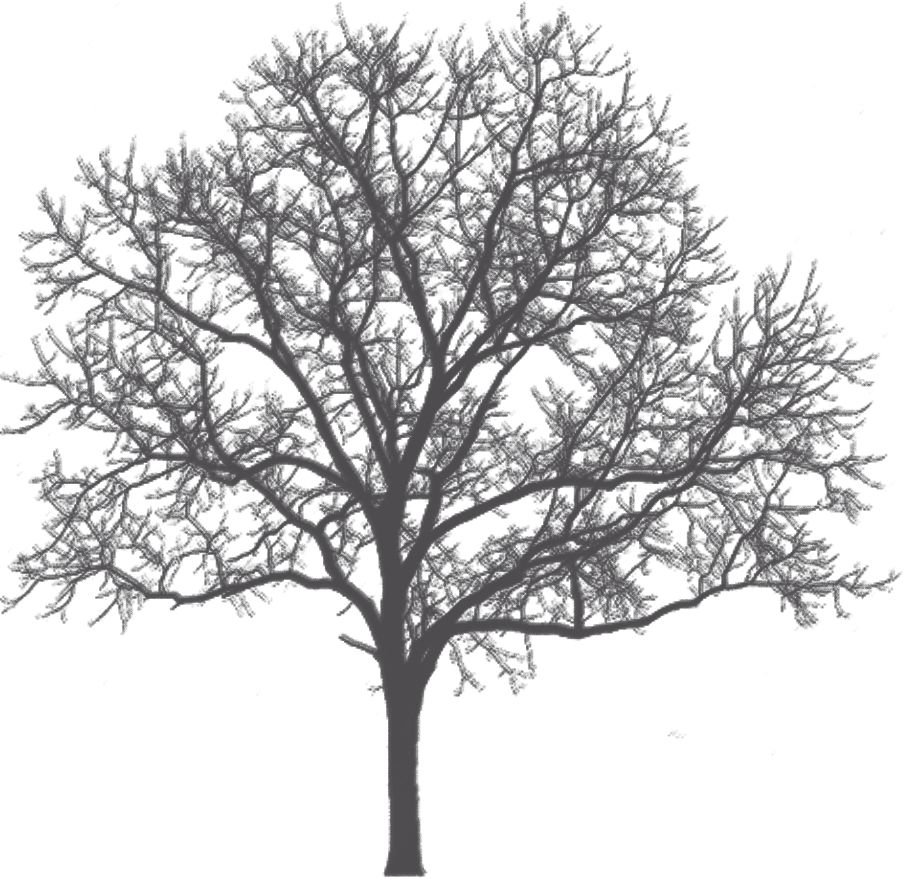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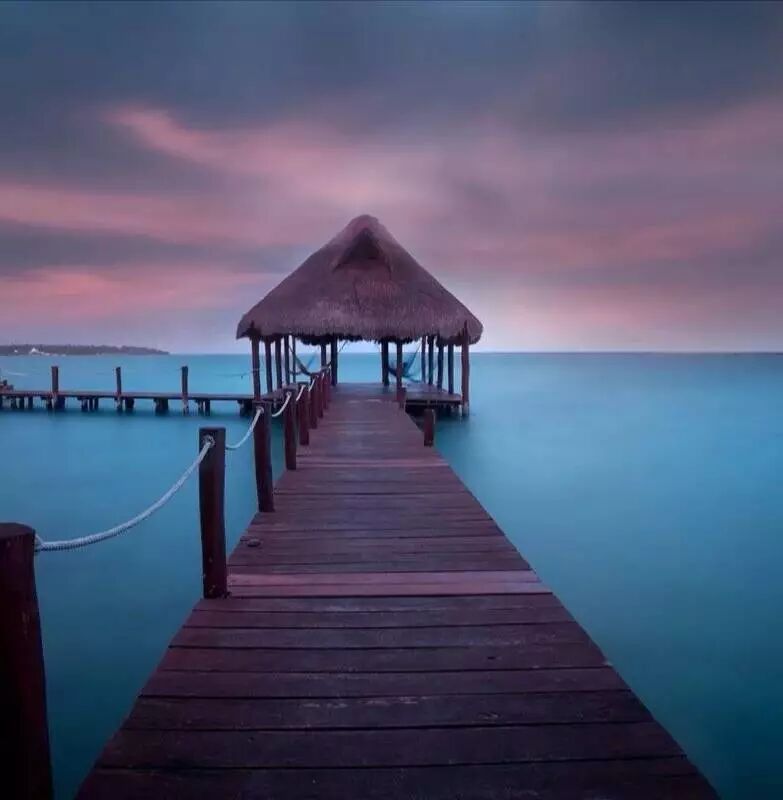
而村上笔下的故事往往发生在大城市,并且刻意以浓厚的世界性掩盖本土性。与村上同时代的另一位作家岛田雅彦认为:“村上春树的作品之所以可以畅销于世界,是因为他在在创作中刻意不留任何民族痕迹,写完后还反复检查,抹去所有具有民族色彩的内容,这样就具有世界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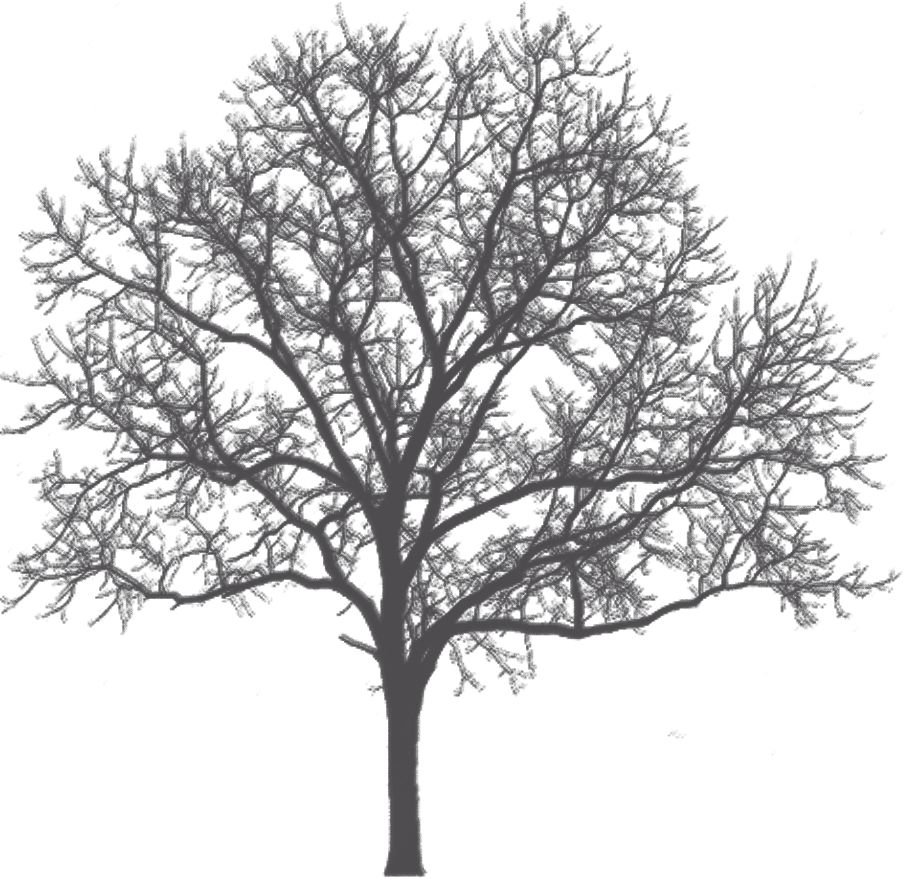

而村上作品在国内的高热度,恰恰是因为不分国界的世界性和对个人的精神世界的细腻关照。
“城市化时代中孤独的个人,以及为了摆脱这种孤独,不断地向着内心深处挖洞,直至与某人联系在一起。”这是村上在许多作品中所体现出的思想和倾向。而这正是处于快速的城市化中年轻一代所面临的问题。
相比上世纪的日本,我国的城市化速度更快,甚至可以说是跳过了若干阶梯的飞跃式发展。这巨大的落差自然会引起人们的茫然,令人感到无所适从。更何况在中国越来越严密的应试教育以及普遍趋向于保守的家长管理下,孤独简直是大多数人青春的代名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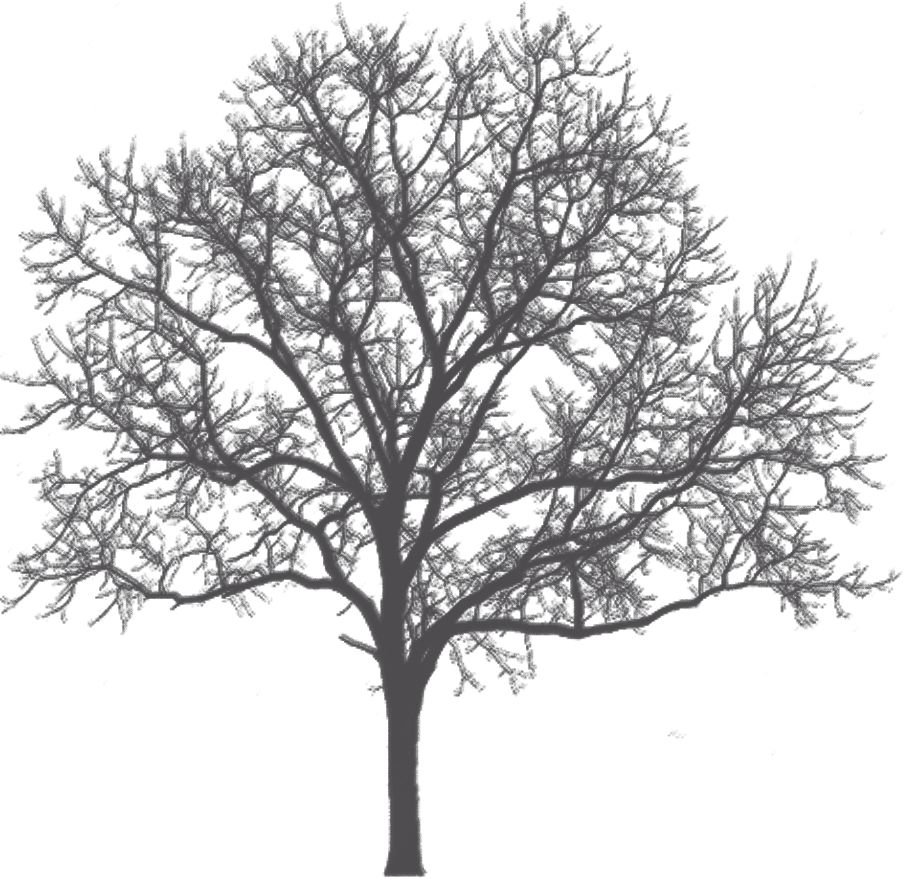

因此,国内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在阅读村上的作品时,会产生十分明显的共鸣。经久不衰的“村上热”恰好反映了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年轻人,特别是城市年轻人心理的变化,并穿越文字与之互动、共振,甚至于相向而行。
村上的作品或许不适合放在诺贝尔奖文学奖这个昭示人文关怀的灯塔上,但它们确实是时代的产物。奖项并非作家的价值的终点,不过读者也应该综合并且客观地评价一位作家,逐渐由粉丝阅读转向理性阅读和深层分析阅读。比起跳脚:“为什么某某没有获奖”倒不如切换到积极角度仔细想想:“为什么是某某获奖了”。
<END>
青年传媒中心文字 / 采编部 章明旻
图片 / 来源于网络
责编 / 事务企划部 韩琳 罗佳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