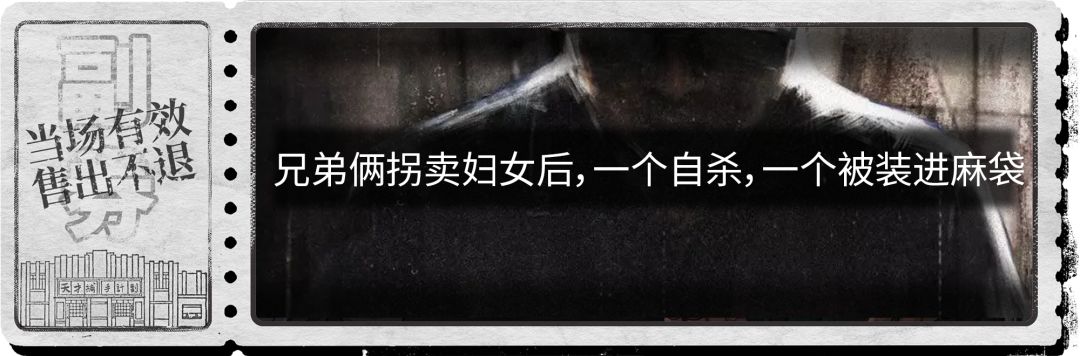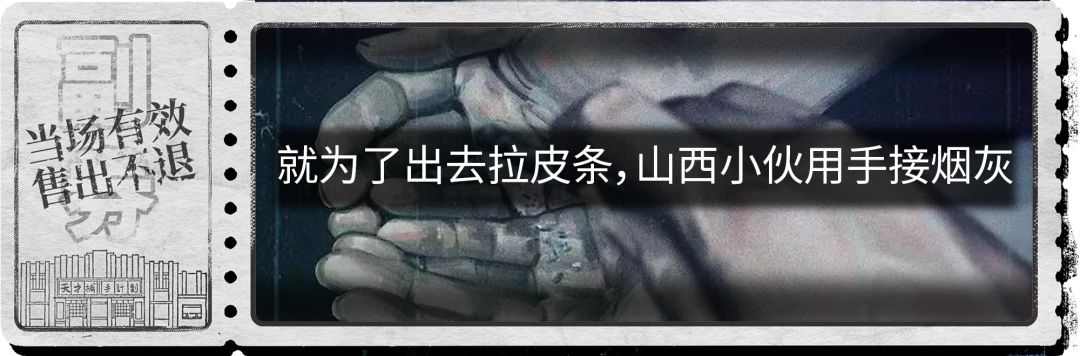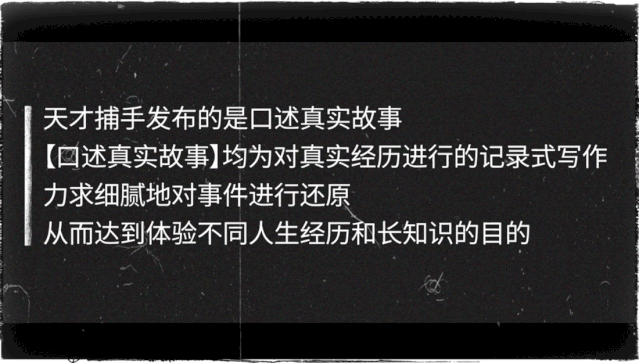
大家好,我是陈拙。
不止一部电影里有这样的场景:有人发出天价悬赏,目标是警察局局长的命。
这种情况真的会发生吗?
两周前,戒毒警察高一丈给我讲了个故事,是他那边公安副局长的事迹。这位副局长的项上人头,被人悬赏百万,还在高速公路上被人追杀。副局长驾车连开三枪,才捡回了一条命。
他会陷入这样的危险境地,就因为一件事儿——警察要打击盗墓。
在那座深埋各种古墓的小城,盗墓行业有时比毒品还暴利。盗墓势力盘根错节,曾有头目放出话来:“敢找我的麻烦,无论多大的官,我让他活不过三个月!”
高一丈原本以为,这辈子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盗墓大案。直到那天,他居然在戒毒所遇到了一个“土耗子”。
从这个盗墓团伙小马仔的嘴里,他知道了那些惊天大案的另一面。
只有小马仔看见的那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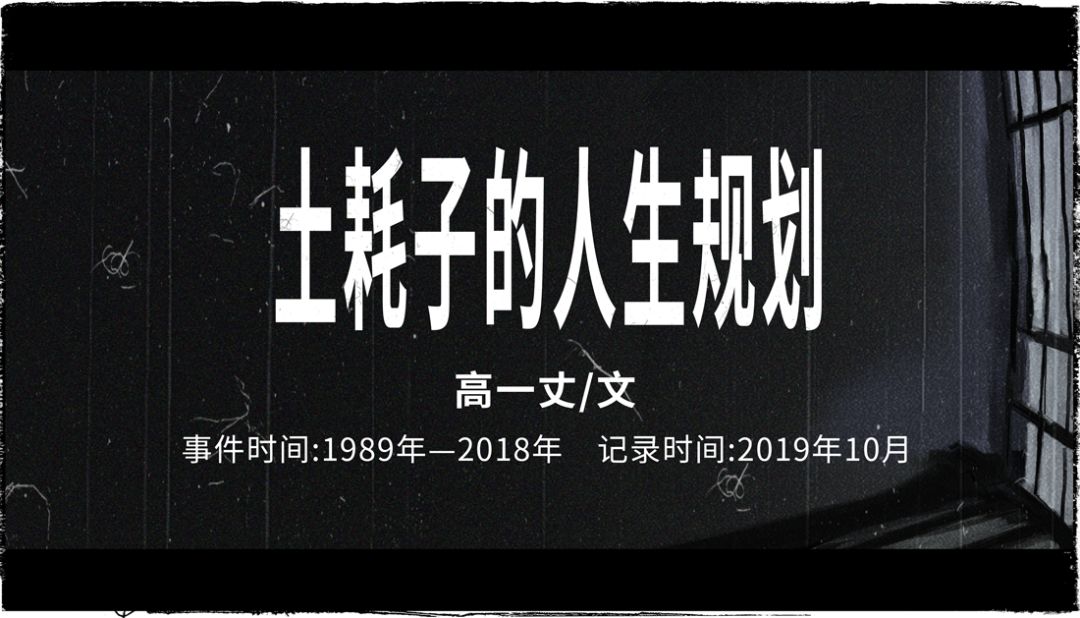
认识福平的时候,他是我所在戒毒所里一个被管教的,被人嫌弃的小老头。
不认识福平的时候,他还是小青年时做过十年“土耗子”——我们当地这样称呼盗墓贼。
“土耗子”带给福平一身疼痛与吸毒嗜好,直至送进戒毒所。不过这个活儿也确实给他带来过一件意外的“真正的宝贝”。

与这件宝贝的缘分是从认识“崩子”开始的。
“崩子”是另外一只“土耗子”。
很多很多年前,那天,土耗子福平正在老板的院子里吃饭,第一次见到了“崩子”。
二人前后脚加盟盗墓老板团队,崩子要早几天。土耗子不挖墓的时候就都住在这个院子里,老板管吃管住,也防备他们单干。
“崩子”是外号,他额头外突,挤得眼睛小小的,当地土话把额头叫“崩楼”,他就成了“崩子”。
崩子比福平小几岁,极瘦,又小,但人鬼精鬼精的。
因为年轻,老板让崩子给土耗子们的伙房买菜进货,崩子就从中鼓捣钱,往上虚报,赚的也就是三两毛钱。他油嘴滑舌,老板知道了也没计较。
崩子八面玲珑,和每个人都能处的来。那时候,院子里的土耗子们没事就聚在一起赌博,赢了钱的,请大家抽烟。崩子要是觉得赢的钱不够烟钱,就会故意放水输掉。
与大多数土耗子一样,福平继续有一单没一单地夜晚挖墓,白天睡觉赌钱。土耗子盗一次墓——不是一个墓,每个墓都要反复盗很多次——的工资是50元,挖出了东西,工资是300元。可以说,挣的是“死工资”。
而崩子除了跟着他们挖墓,还跟着老板找买家。
每次在交易之前,崩子晚上总爱跑去买主房间,说能帮买主跟老板说说情,便宜一些,但他要一笔好处费。出手文物都有估好的底价,比如卖20万,会报25万,讨价还价也有空间。成交价格便宜一些,买主会觉得都是崩子的功劳。
崩子挣的是“活钱”,还收了人情。
福平入伙则完全是靠力气。福平八九岁的时候得过癫痫,耽误了念书,一辈子只会写自己的名字。他很早就不愿意像祖辈一样土里刨食,他想出人头地。
他有的是力气,十几岁时就在山上背石头了。那时候走山路用不了平车,运输石头就靠人力背。那些石头是用炸药炸出来的,大的有一百来斤。石头上的尖棱子多,扎在背上,全是“血窟窿”。
福平在戒毒所看病时,曾拔衣领给我看,他背上满是密密麻麻的,泛黄的伤疤。我当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福平却得意地笑:“哈哈,背一趟石头下来,能挣2分钱哩。是高收入!”
崩子对福平不算好,也不算坏。“他就是嘴甜眼尖,会来事儿。”

不久后的一个半夜,一行人又开工了。那次有福平,也有崩子。
那个墓不大,已经被别人盗过两三回了,老板没抱啥希望,只是想再去看看,能不能拣拣漏。
墓坑就在一个镇子边的山上,四下无人。
这几乎就是个空墓,很方便进去,他们就挖了起来。没想到,刚开始没多久,就挖出了一个青铜壶,不大,半尺长,看着老旧。
土耗子们都非常高兴的,挖出了东西,当天的工钱就是300元了。
就在大家都欢欣鼓舞看青铜壶的时候,没人发现墓底还有两个人,福平与崩子。
他俩不是约好的,而是福平有气力,崩子眼尖但太瘦弱,挖不动。所以老板就让他俩搭伴。
那天,他们带了盏煤油灯放在墓底。
突然,眼神好的崩子又发现了一个“干缝缝”。
“干缝缝”是吉兆。这里的古墓文物以青铜器为主,青铜在泥土里会吸水生锈。那时没啥金属探测器,在潮土里找见一个“干缝缝”,土耗子就会死命挖。“保不齐是金贵东西。”
刨是福平的活儿。没几下,土里就露出个尖尖——一个“刀币”的尖尖!
崩子和福平挨得很近,看见尖尖,福平特兴奋,崩子却立刻给他使了个眼色。压低声音咬耳朵——“先别往出拿!”
福平一下就明白啥意思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崩子就用湿土把刀币那里给糊上了。
他俩还嘀咕了几句,算了算老板磨着不发工资多久了。但爬上来,福平开始害怕,“心都提起来了。”
福平知道,瞒着老板私藏文物,惩罚非常重。他听说有个土耗子,把文物“片片”偷夹在布鞋的千层底里。结果被发现了,大老板找了两根长钢针,从他的鞋面扎了进去,直到把他的脚扎穿。黑话叫“穿黑牛鞋”,因为布鞋是黑的,两根钢针就像两根牛角。
按规矩盗完墓,最后一个人要“清”一遍墓坑,大一点的东西,根本藏不住。不过,因为这次有那个青铜壶做“掩护”,老板的注意力显然不在他俩身上。
福平与崩子俩人的黑布鞋安好无恙。

这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事儿了,而福平盗墓更早,是从80年代末开始的。
那时,县里发生了几件“大事”,来了好几拨北京的考古专家,真有老物件被挖了出来。
“地底下有值钱的古墓子!”这个消息就像一瓢水倒进了热油里,在当地传得沸沸扬扬。没过多久,县里来了一伙——“南蛮子”(农村对南方老板的叫法)。
南蛮子们穿得光鲜亮丽,表面上是来投资做生意的,私底下干的却是盗墓的营生。他们需要壮劳力,福平经亲戚介绍,成了他们手下的“土耗子”。
这股盗墓潮引来了南蛮子,引来了小县城少有的几辆小轿车。几家稍微有档次的饭店竟然都开始上南方菜系了。盗墓潮还引来了那时连市里都没有的歌厅,生意火爆。
只见过山上的大石头,没见过大钱和大场面的福平被惊到了。南蛮子拥有的一切,让他羡慕得不得了。
“当时我觉得,就算给南蛮子提鞋,也得不少钱!”福平后来在戒毒所对我说。
福平第一次盗墓,是在一个后半夜。
那时他啥也不懂,按工头的指示下了墓坑。进了坑里,他们才敢点亮装着煤油的马灯。福平学着样子,在里面瞎刨了一通。但两三个钟头,啥也没找见。
“八十回能挖出来一回,就算走了鸿运了!”工头点了两根烟,递给福平,“自己抽一根,那根敬一敬‘老骨实’(墓主人)。”
我后来问福平,你第一次盗墓是什么感觉?福平想了想,说:“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就像是给别人打地窖。”
每次盗干净了一个“地窖”,南方老板就会找个翻斗子车,把土耗子们拖进澡堂“洗晦气”。说是洗晦,其实就是去玩。那几年,县里色情业发达,老板和土耗子们不知道祸害了多少女娃。
那时,福平还年轻,心劲大,对埋在地底下的文物特别好奇。当然,更让他激动的是无论挖不挖得到东西,都能拿到钱,而且远比过去背石头挣得多。
“买卖”好的时候,福平他们一个月能盗5、6次。运气好一点,干个把月,就够买上一台三蹦子车。
而南蛮子贩卖文物的收入更是吓人。福平说,九几年的时候,有一伙儿南蛮子挖出了一个小青铜鼎。“成色好,单单一个就卖出1000多万。”
这个天文数字,福平连做梦都不敢想。
“老板们真威风啊!有钱有势,每天有人围着,啥事情都能平。我也做过那种梦,实际上,我球也揽不成。”福平说。
不过,福平很喜欢这群“南蛮子”。他认为他们人好,讲信用,不拖欠工钱。

其实,在遇到崩子前,福平已经学会 “捡漏” 了。
至今福平都能背得出当时他们“盗墓圈”里的那个顺口溜——
一兵推个浅壕壕,青铁蹦蹦卡腰腰;
二兵刨个小窟窟,背出一篓好壶壶;
三兵挖个深窑窑,横竖都是断削削……
五兵拓个宽房房,淹死一窝窝,婆姨抛下泪颗颗。
“兵”就是土耗子。因为大多数的土耗子都不专业,第一波挖开墓穴的人,很少能把随葬品拿干净。后面来的耗子,运气好的能找到更值钱的宝贝,运气差的,挖塌了墓穴,死在里面也是有的。
在戒毒所里,我问过福平,“四兵那一句说的是啥?”福平想了老半天,没记起来。
那时候,盗墓俨然成了县里收入最高的营生。不知不觉中,这个县城里的一些东西变了。
福平跟南蛮子学艺的那个阶段,“盗墓”成了当地人每天茶余饭后的主要谈资。“哪里挖出个什么东西”、“哪里的古董又卖了多少钱”;另外,一些女人为了钱,甘愿贴上去做南方人的情妇。
地下的文物重见天日,在这个县城里搅起了一股风潮,而且来势汹汹。
1994年,当地公安部门查得严,风声紧。南方老板给土耗子们结完工钱就跑了。一些胆大的本地人看见盗墓有大把的钱赚,又开始组织人马,非常猖獗。
有经验的福平又被人招了去,他有了新老板。
“口子开了,东西就在地底下,你不挖,有的是人挖。跟着本地人也好,攀亲搭挂的总有点联系,不像南蛮子抹屁股走人,好摊子、烂摊子都没人收。”福平当时这样想。
当然,福平更知道自己没文化,没手艺,只有当土耗子的本事,还永远翻不了身。
“你见过土耗子‘逆袭’成老板的吗?”后来我问福平。
福平想了想,抿住嘴摇头,“那是天生的!”
本地的新老板们更希望快点出东西,出更多的东西,但又怕工具破坏了文物。他给土耗子们规定:“五尺以下,就得用手刨。”
戴着线手套,日积月累,福平的指甲还是没保住。刚开始是指肚肿得憋胀,刨多了,指甲就磨成了薄片。黑泥一点点往里渗,挤出脓水,时间长了指甲裂开,最后就脱了。
在戒毒所里,我还特别观察了福平的手——除了他的大拇指还有指甲,其他的手指,都是一根根黑紫色的肉咕嘟。粗糙,结着厚茧,正常人绝对不想再看第二眼。
“指甲再也长不出来了。”福平说:“前几年过年,我给家里挂挂历,图钉扎进去半截,我都没感觉。”
不过,虽然90年代福平就学会了“捡漏”,但是他不敢——直到遇到崩子。

藏好刀币,崩子和福平等了两天,老板正好去了外地。
当晚,他俩在离墓穴不远的山洼里藏下来。他们怕被人看见,全程不敢用手电。快到黎明,天蒙蒙亮。两人奔向那个墓穴。
崩子身轻手快,下墓取货,福平在地面放风。没想到,不是一枚——是六枚!
青铜刀币最怕氧化,崩子还特意带了油布把它们包起来,又在外面裹了半张干羊皮。
本县的名字很有来头,是汉武帝起的,有2100多年的历史了。地下有不少古墓葬,随葬品以青铜器为主,文物价值非常高。
就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刀币,就有“齐刀”、“燕刀”和“赵刀”之分。当时,这个古墓边上的小山坡上,崩子与福平完全不懂行情。但多年后,一枚“齐刀”在拍卖市场上被拍出了200多万人民币的价格。
“我去找个懂行的看看成色,回来对半分。”崩子提议,一拍即合。
二人迅速撤离。
不几天,脑子灵有门路的崩子就告诉福平:这六枚刀币是战国时期的,很珍贵。
崩子爽快地分给了福平三枚刀币。
拿着第一次属于自己的“捡漏”,福平特紧张。他也学着用油布包裹刀币,还拿蜡水封住口。
回到家,福平把封好的刀币粘在自己那个大木头箱子底下。他盘算:“十天,十天没有动静,这事情就保险了。”
结果,没过两天,崩子竟然跑了!老板很生气,找到崩子的舅舅。
偷藏刀币的事,崩子舅舅知道一点,在头头的威逼利诱下,他把福平供了出来。福平后来的猜测是:崩子舅舅和崩子在一块住着,崩子要走,觉得一时半会估计再回不来了,就和舅舅说了。
老板随即领人到了福平家。
福平一见吓得半死,哆嗦不止,他以为自己藏刀币的事败露了。老板二话没说,上来就冲福平面门甩下一巴掌,然后大声问:“崩子去哪了?”
虽然疼,但福平一下就放心了。他知道,老板以为6枚刀币都在崩子那。
老板把福平打了个半死,当场就断了他一根肋骨。最后甩下5000块和一句话——“滚吧!以后不用干了。”
福平当时心想,其实老板不是怕崩子拿了点东西,而是怕他着急出手,走漏了风声,让别人给盯上。

1997年,福平的盗墓生涯结束,不过他还藏着那3枚珍贵的战国刀币。而当地老板们,在这块土地上越干越热闹。
本地老板都是地头蛇,不知收敛,势力逐渐扩大。最大的那个老板不仅盗墓,而且涉黑。只要别人发现了价值高的古墓,就派马仔去抢。他控制了的区域,别的盗墓团伙休想插手。
盗墓老板的触角甚至伸向了警方。
有人监视新来的县公安局局长,他办公室的灯光什么时候亮,什么时候灭,老板们都知道。看监控的辅警被拉拢腐蚀了,甚至有民警加入团伙,在现场指挥盗墓的时候被抓获。
很长一段时间,警方都是顶住重重压力,花了很多心血,才把内部这股势力彻底剪除。但经过多年的疯狂盗掘,当地很多墓穴被洗劫一空。盗墓团伙先后盗出了多种青铜器,有鼎、尊、斝(音甲)、兽形觥……年代久远,能追溯到商。
有土耗子向警方交代,他们挖到最大、最贵重的文物,是四口青铜钟。盗墓那么久,他们从没见过那么高档的兽面衔凤纹。最大的那只钟有56公斤,最小的那只有点残。三只品相完整的钟经过层层倒卖,最后被一个香港的收藏家高价买走。
这个行当的风起云涌,却早就和福平无关了。
结束了近十年的盗墓生涯之后,土耗子福平难得过起了太平的日子。
2000年左右,他用盗墓积攒的钱在市里买了套小房子。因为不识字,他找不到好工作,就在一个单位家属院当门卫,也还不错。这一干就是6年。
过去盗墓的经历,对福平来说就像一场梦。在这场“梦”里,他还娶过三个老婆。
十七岁时家里给安排了一门亲事,福平娶了媳妇,日子不宽裕,但安安稳稳。他们不懂什么近亲结婚,生下了一个男娃,是个“怔子”(傻子)。请土医花了不少钱,却没有一点效果。他家迷信,认为福平娶得不是正经媳妇,把媳妇和孩子赶出了家门。
挣了几年盗墓的钱,福平娶到了第二任老婆,是县城裁缝铺里的小工。福平为了让老婆安心,一直瞒着,只说自己跟老板打工。
福平知道盗墓风险大,除了那一套迷信的说法,最怕公安抓。毕竟盗墓是重罪。
那时候,公安夜里都在巡查。大巡逻车的车顶上架着一个高瓦数的探照灯,灯光打过去,哪里有土灰扬起来,十有八九,那里就有盗墓贼。
那次,半夜两三点,他们在某镇的一片黍子地里动手,遇上了警察突袭。
福平撒腿就跑,不敢往回看,一直低着头往前冲。跑了很久,他进了半山腰的一个村。借着月色,他看见有个院子,想翻进去躲一躲。结果他翻进去一只脚踩空了,身子一歪,摔在地上,把大腿摔断了。
被朋友送回家的时候,福平的大腿已经肿得脱不下裤子了。“硬是拿剪子剪开的。”
那天晚上,不少土耗子被抓。福平不敢去医院,在老婆逼问下,他才坦白了盗墓的事。等他伤养好了,第二个老婆和福平大吵了一架,也走了。
福平留下了后遗症,走路有点跛,加上盗墓留下的各种伤痛和阴冷,一变天,就疼得不行。
也就是那时候,福平托人买来海洛因“止疼”,从此就没断过。
2004年底,福平认识了第三任老婆,按他跟我说的就是:“没啥爱情,就是互相找个伴儿。”
第三任老婆知道福平盗过墓,但没觉得有什么。不过吸毒,门卫的工资就远远不够了,加上盗墓落下一身病,多年积攒的家底渐渐败光。老婆因为这事,天天和福平吵架。
有一次他们又大吵一架,福平终于忍不了了,说出了自己还有刀币的事——“只要出了手,肯定卖个好价钱。”
那三枚刀币一直妥妥压在大木箱子底下,后来福平告诉我,“那地方最保险,没人动。”
这是2007年的事儿了。

十年后。2018年2月8号,我第一次见到了福平。他因吸毒被抓,第三次进入强戒所。
同一批学员当中,他年纪最大。头上的“白毛”剃短,套上大号的“校服”,像个老旧的电线杆。
但这个“老电线杆”很不老实。
入所体检时,年轻女护士问他的既往病史。福平满脸奸笑,“呀,痔疮算不算?挺严重的,大夫,你要不要看看?”护士无语,我走上前,用对讲机拍福平的脸,“回去我给你看,信不信让你脸上再长一个?!”
他这才不情愿地低下头。
“对于有些学员,简单粗暴的话往往更管用。”师傅曾经告诉我。与福平的第一次谈话,我就警告他。
福平嘻嘻一笑,“嗨呀,队长你可放心吧,我这人最老实了,绝对不会给你们添一点事!”说完,嘴一呲,露出满口黑黄的牙。
戒毒所学员“成色”分明。一般来说,“头进宫”的听话,畏惧强戒所,所以要让他们变得胆怯,绝对服从。而“多进宫”的学员,几乎个个都是滚刀肉,摸清了里面的套路,油滑多了,大部分时间就琢磨怎么偷懒,占小便宜。
福平承诺的“老实”,只维持了两天。
福平零花钱账户上没有一分钱,他仗着年龄大,偷别人的烟。宿舍组长来我这抱怨。我抬头看福平,他正佝偻着身子,在工位上不停摆弄着手里的线圈。
我叹了口气,告诉组长:“一两根,能给就给吧。抽了烟心里舒坦点,别惹其他麻烦。”
可福平不仅不领情,他还“飘”了。
那一天,他竟在我眼皮底下偷管教的苹果。
当被我叫住,福平反倒质问起我来。
“队长,这水果不是给学员们吃的?!”
“嗨,高队,我以为是要发给学员的。我把脑子抽坏了,迷糊了,迷糊了!”
我的火气“蹭”地一下被点燃了。隔着值班台,差点把他揪过来,师傅在一旁扯了我一下。
我把他偷的那两个苹果分给为我们洗水果的学员吃。五分钟不到,福平就和他们打了起来。福平扯着嗓子叫:“是他俩先骂的我!是他俩先骂的我!”
监控视频里,身高臂长的福平甩开胳膊,对着那两个学员来了一顿王八拳。俩人手里端着盆,根本招架不住。
被打的学员说,福平故意咳出一口痰,吐到他的苹果上。福平立刻大声狡辩:“我是故意的?谁没个咳嗽的时候了,我正好嗓子痒不行么?”
我用电警棍指着福平,再次警告他闭嘴。福平却突然憨笑起来,“唉,队长,犯不上。”他一边说,一边顺势把电警棍往下按。
这个动作非常危险。曾经有管教的警用装备就是这样被学员抢夺过去的。情急之下,我要打开电门,师傅比我反应快,从背后拽着福平的衣领,把他使劲往后一扯。福平没站住,身子往后一倒,故意把脑袋磕在地上,耍起了装晕的把戏。
后来,福平受罚,引得其他学员一阵哄笑。大家都讨厌他。

2018年国庆节刚过,轮到我值夜班。天气比白天冷的厉害,戒毒所值班室的空调老旧,声音大,不出热风,我抱着本书,独自坐着,胸腔里有种说不出的憋闷。
“报告!”突然,有人在铁门外大喊一声。
我抬头一看,是惹人嫌的福平。于是板起了脸,皱眉问:“你,有啥事?”
我手指一点,打开了值班室铁门的开关。
福平进了屋,悻悻地半蹲下,“队长,我不认字,你看报纸上有没有盗墓贼的新闻?麻烦你给我说一下,某县那边的……”
说着,他小心地展开手里的报纸。他的手指头,除了大拇指,其他都没有指甲,只是一个个黑紫的肉咕嘟,粗糙,还爬着厚厚的茧疤。
他抬头,抬头纹摞了几层,眼巴巴看着我。

我不想看他的脸,接过那期《法制报》,大概扫了一眼。在一个豆腐块大小的角落里,还真找到了一则关于盗墓案件的报道。
没等我开口,福平就着急地问——
“判,判了几年?”
“20年,怎么?你家亲戚?”我把报纸甩在值班台上,瞪福平。
“20年!”福平把嘴合上,愣了一下神,“不是我亲戚。”他躲开了我打量的目光,“实话说,我之前干过盗墓……”
从当天晚上开始,连续好几个夜班,我都在监控里看到福平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渐渐地发现,福平好像有些变了。
他开始会害羞。福平屁股上长了一个大瘤子,大夫叫他把裤子脱下来,他却犹豫,有点难为情;可能是哪句话让福平觉得我和大夫真的在关心他,他破天荒地对我们说:“真是麻烦你们了!”
这个三进宫的老学员,似乎没之前那么飘了。但我总感觉他有些心不在焉的。
那几天,我坐在福平旁边陪他输液。实在太无聊了,我就问他:“前几天你为啥跑出来,让我帮你找报纸上的新闻?”
“嘿嘿”。福平先是笑了两声,接着又叹了一口气:“唉,我不认识字。在里头人缘不好,问别人,他们都不搭理我……”
“为啥找某县盗墓案子?”我潜意识里觉得他和这个案子可能有关,但我不确定福平是否会跟我说实话。
福平坐直了身子,给我讲了他的故事。故事里有“土耗子”,有“南蛮子”,有“崩子”,还有他的三任老婆。当然,更少不了那三枚珍贵的战国刀币。
福平和第三任老婆吵架,说出藏了三枚刀币的事儿,纯属意外。
盗墓这行门槛很高,基本没有普通人能干这个的。福平说,第一要有“关系”,这是犯罪,要能保住自己,不然有命赚没命花钱;第二得有本钱,挖墓养一群土耗子,睁眼就是花销。
不过与“盗”相比,“出”的风险要高出许多倍。特别是土耗子私藏的东西,极难出手。
福平清楚,在老板那里,盗和销是分开的。贩卖文物的圈子就那么大,谁出手了什么东西,立马就能倒查出来。本地最大的老板,曾经查出了一个私藏东西的土耗子。他们直接把那件青铜器熔成水,往那人胳膊上浇。
从1997年崩子逃走,到自己被打歇手。过去十年了,福平没走三枚刀币的丝毫风声。
不过老婆知道了,“打击盗墓”的声响消了些,福平又想起了那句话——富贵险中求。
2007年,福平开始打听。
他找到一个太原收古董的二道贩子。一打电话,对方一听他是某县的人,就立即邀请福平去省城。
他俩在西山矿务局的一个宾馆里见了面,二道贩子一看刀币就说:“好东西!卖个二三十万应该没问题。”
二道贩子很快联系到一个北京的买主。买主亲自赶过来看品相,还带着一位验货专家与检测仪器。
万万没想到,不到一天,检测就出了结果——三枚刀币都是仿制品,铜绿是做旧黏上去的。
北京买家大骂福平是骗子,福平整个人都懵了,他一直质问验货专家,是不是给他掉包了。
专家说:“全程你都跟着,做个一样样的假的,哪能这么快?”
那三枚刀币上做旧的铜绿使劲一捻,就整块掉下来,福平摸了摸,还有粘着的细胶。
福平心里咯噔一下,知道不对劲了——当年,崩子掉了包!
挖出来六枚刀币时,福平只看了一眼。因为怕被别人发现,没记住是什么样子。后来崩子给他的时候,他没觉得不对劲,只顾着激动了。
本来还想着在省城买点东西给老婆捎带回去,结果啥心思也没有。他去车站坐上大巴就回了老家。
他老婆那最后的一点希望也破灭了。女人哭闹一场,也走了。
揣着三枚赝品,福平成了孤家寡人。我问他后悔最初抛弃了那个孩子不,福平搓了搓大腿,“傻不傻总是个伴儿。前几年我也打问过,根本没音讯,也就死心了。”
崩子的下落,福平没有刻意去打探。有次回老家,顺带问起来。听人说,崩子在外地成了家,干买卖,具体情况也无从考证。
那天,听我读报纸上面二十年的判决的时候,我不知道福平心里究竟想到了什么。他当时拿上报纸,只说了一句话——
“谁也没有好下场,再厉害的人也跑不了。我们当地偷佛头的人,因为各种报应,都死的差不多了。”
其实,骗了福平的不是刀币,而是人心。
崩子当初掉包确实是要坑福平,但现在看,这说不定就是救了福平。至少福平现在不是在监狱里,而是在戒毒所。

福平和第三任老婆吵架,说出藏了三枚刀币的事儿,纯属意外。
盗墓这行门槛很高,基本没有普通人能干这个的。福平说,第一要有“关系”,这是犯罪,要能保住自己,不然有命赚没命花钱;第二得有本钱,挖墓养一群土耗子,睁眼就是花销。
不过与“盗”相比,“出”的风险要高出许多倍。特别是土耗子私藏的东西,极难出手。——应该是“出货”。
福平清楚,在老板那里,盗和销是分开的。贩卖文物的圈子就那么大,谁出手了什么东西,立马就能倒查出来。本地最大的老板,曾经查出了一个私藏东西的土耗子。他们直接把那件青铜器熔成水,往那人胳膊上浇。
从1997年崩子逃走,到自己被打歇手。过去十年了,福平没走三枚刀币的丝毫风声。
不过老婆知道了,“打击盗墓”的声响消了些,福平又想起了那句话——富贵险中求。
2007年,福平开始打听。
他找到一个太原收古董的二道贩子。一打电话,对方一听他是某县的人,就立即邀请福平去省城。
他俩在西山矿务局的一个宾馆里见了面,二道贩子一看刀币就说:“好东西!卖个二三十万应该没问题。”
二道贩子很快联系到一个北京的买主。买主亲自赶过来看品相,还带着一位验货专家与检测仪器。
万万没想到,不到一天,检测就出了结果——三枚刀币都是仿制品,铜绿是做旧黏上去的。
北京买家大骂福平是骗子,福平整个人都懵了,他一直质问验货专家,是不是给他掉包了。
专家说:“全程你都跟着,做个一样样的假的,哪能这么快?”
那三枚刀币上做旧的铜绿使劲一捻,就整块掉下来,福平摸了摸,还有粘着的细胶。
福平心里咯噔一下,知道不对劲了——当年,崩子掉了包!
挖出来六枚刀币时,福平只看了一眼。因为怕被别人发现,没记住是什么样子。后来崩子给他的时候,他没觉得不对劲,只顾着激动了。
本来还想着在省城买点东西给老婆捎带回去,结果啥心思也没有。他去车站坐上大巴就回了老家。
他老婆那最后的一点希望也破灭了。女人哭闹一场,也走了。
揣着三枚赝品,福平成了孤家寡人。我问他后悔最初抛弃了那个孩子不,福平搓了搓大腿,“傻不傻总是个伴儿。前几年我也打问过,根本没音讯,也就死心了。”
崩子的下落,福平没有刻意去打探。有次回老家,顺带问起来。听人说,崩子在外地成了家,干买卖,具体情况也无从考证。
那天,听我读报纸上面二十年的判决的时候,我不知道福平心里究竟到了什么。他当时拿上报纸,只说了一句话——
“谁也没有好下场,再厉害的人也跑不了。我们当地偷佛头的人,因为各种报应,都死的差不多了。”
其实,骗了福平的不是刀币,而是人心。
崩子当初掉包确实是要坑福平,但现在看,这说不定就是救了福平。至少福平现在不是在监狱里,而是在戒毒所。

福平在我们戒毒所医务室输液的那段时间,电视里正在播放《中国诗词大会》。
福平没文化却看得津津有味的,他感慨:“人家的诗写得真好,可惜我不认识字,老祖宗发明了那么多字,我就认识自己的名字。”
我被他的话逗笑了,“你都50多了,早没想明白?”福平也笑着告诉我,“还真的是没早想明白。”
他突然跑题,“我一直觉得,我成了现在这个样子,都是因为我没钱,没本事,没势力。那些盗墓的大老板一辈子保准吃香喝辣,啥也不用发愁。我本来已经认了,是我没那个富贵命。”
福平顿了顿,又说:“前几天看见我们那边最大的老板被判了20年。那个人,是我以前做梦都想变成的人。当时我才一下明白,做过坏事,谁也跑不了,这才是命!”
“善恶到头终有报。”我附和了一句,不知道福平能不能听懂。
福平的病好了以后,竟然开始学习认字了。他找到给大队出板报的一个学员,让他来教。
福平没钱,也没什么可以作为交换的。他就把自己一年一次的,有红烧肉和大鸡腿的生日餐让给教他认字的学员吃,充当 “学费”。
福平还时不时地找我聊天,我问他为什么要识字,他考虑了一下,认真地说: “我今年五十,一辈子屁本事没有。出去以后,我起码还有20年的活头吧,就算不会用手机,至少学会了,也能看个报纸啥的。”
“我这回出去,料子也不抽了,真没啥意思。以前闲着就闲着,真不如给自己找点事做做。”
这番话从一个三次强戒的学员口中说出来,我真有点不敢相信。但我还是选择相信福平,因为他早就没有减戒期的资格了,也没有必要来诓骗我。
“你要愿意,我再给你找个老师,学门技术吧!”
福平脸上的褶子一下堆了起来,他高兴地直点头,“能行,能行!这个好,这个好!”
我让福平跟一个做过电工的学员学维修。他们在一起摆弄不良的线圈,清理阻塞的气泵。福平的手指虽然没指甲,但还蛮灵活的。
在戒毒所,学员参与生产劳动能获得一定的报酬,维修岗位的劳务工资会高一些,一个月120块左右。这笔钱会直接转到学员零花钱的账上。
我想让福平出所的时候,多拿一点钱去生活。而福平似乎也明白我的用意,他的零花钱,从来没有买过烟。
前段时间,福平突然问我:“队长,您去过五台山吗?”他说出所以后,想把市里的房子卖了,去五台县养老——
“住得离菩萨近一点。”
“你一个盗墓的,还信这个?”我跟他开玩笑。
“人总得有个信的东西。”

福平的故事,让我想到了一个讲“小人物”的电影——《大佛普拉斯》。
里面的主人公,是一对拾荒者和看门人,不曾被人多看过一眼。每当他们出现在银幕时,镜头都是纯黑白色的,就像他们的人生底色。
而电影里的彩色拍摄画面,都是在记录一位富豪老板的“日常生活”。
有一天,拾荒者和看门人太无聊了,偷偷看了富豪的行车记录仪,里面是富豪老板杀人的经过,这就遇到了一个“大事件”,大事件把当地供奉的大佛都卷了进来。很快,看门人被残忍灭口,拾荒者收到了死亡威胁,惶惶不可终日。
两个“小人物”因为意外参与了“大事件”,人生陷入了厄运。
他们人生的容错率太低了,福平也是这样,因为三枚刀币,卷入一场了惊天大案。
福平比别人更幸运的一点是,他的刀币是假的。如果真的刀币经他之后流入市场,他的人生,大概也随着盗墓团伙的覆灭而被捣毁了。
现在,他终于不用再惶惶不可终日了。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扫地僧 罗十五
插图:超人爸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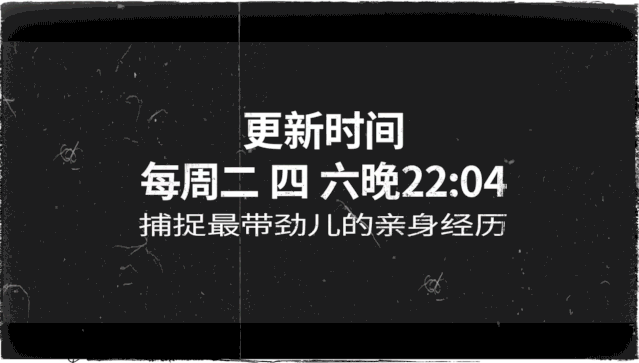
点击下面链接,观看更多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