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凡的杀手背后是不甘平凡的李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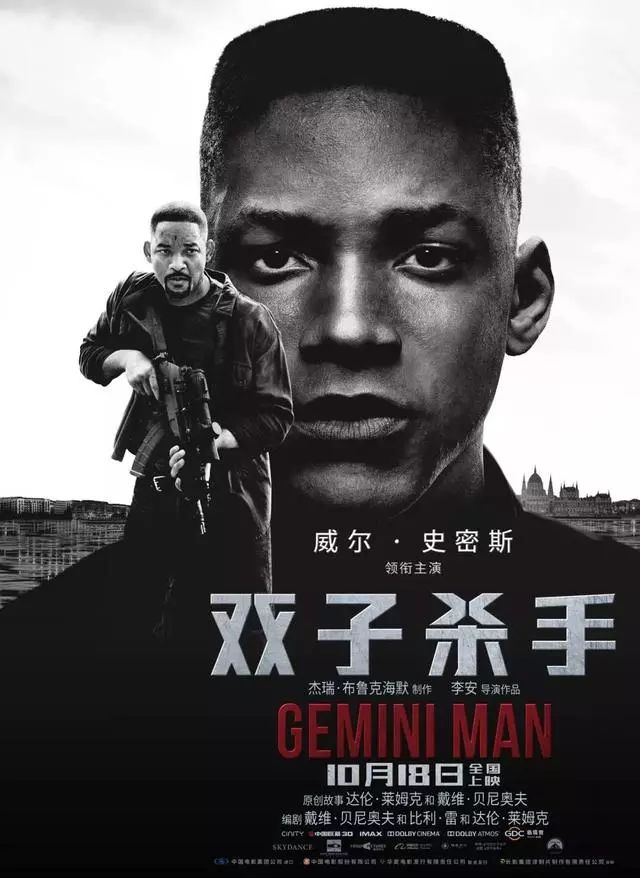
《双子杀手》电影海报
因为热爱电影事业,65岁早已功成名就的李安,依然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

《双子杀手》已经不是他第一次采用3D、120帧/秒、4K分辨率的高格式拍摄电影。2016年《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同样用这种模式拍摄,在映前就吊足业界和观众的胃口,但映后评价却不如预期,可以说这是一次技术大于艺术的失败尝试。当时《比利?林恩》商业回报遇冷,3年后他没有气馁,带着《双子杀手》卷土重来。
![]()
李安语言平实却自有力量
2006年,李安凭借《断背山》首次摘得奥斯卡最佳导演,也是首位获此殊荣的华人导演。2001年,他的《卧虎藏龙》也代表华语电影,拿下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此后,他却爱上了电影视觉技术革新。2012年,他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使他夺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和最佳视觉效果奖。《比利?林恩》和《双子杀手》是在《少年派》的极致3D技术上,升级了帧率和分辨率。

念戏剧出身、且擅长讲故事的李安认为:电影艺术已走过百年,但叙事方式、拍摄方式,以及24帧率的呈现依然裹足不前。
电影新技术,尤其是120帧对他而言,具有很大的好奇心去追求。但我所在的厦门和全国很多地方影院,目前都无法达到3D/4K/120帧,只能达到3D/4K/60帧的版本放映。传统电影都是24帧/秒,帧率提升无疑带来逼真清晰的画面细节。帧率和分辨率的提升,使得画面亮度色彩更丰富。

画质的提升也带来真实度的提升,动作戏的细节观感流畅得纤毫毕现,着实过瘾。
李安改变了传统的动作戏拍摄手法,摒弃24帧电影动作戏快速剪辑、横向移动镜头、手持摄影等技术处理方式。他采用高帧率跟拍长镜头、角色主观镜头、慢镜头等手法,使得高速运动状态下的人物和动作流畅,面部表情变化自然,尤其是体现在摩托追车和打斗戏中。

另外,电影的技术突破,还体现在数字视效创造出来的全CG形象——年轻版的杀手小克(威尔?史密斯饰演),视觉技术的以假乱真,让人不由得想起《阿凡达》潘多拉星人,《指环王》咕噜,《猩球崛起》凯撒,《狮子王》辛巴,《奇幻森林》男孩毛克利等。《双子杀手》开场是高铁进站的场景,紧接着这辆高铁飞驰而过的超广角畸变镜头,瞬间移动的质感仿佛高铁真实地从眼前闪现,好像呼应了1895年的老电影《火车进站》。这辆高铁就像李安内心的镜头语言,使得百年前的影像和现在的影像交相辉映。

剧情拖沓沉闷但指代深远
视觉技术大跨步向前的同时,电影却输在了沉闷的剧情上,克隆人题材并非新鲜话题。李安试图探究克隆人与被克隆人之间、既熟悉又陌生的微妙关系。51岁的杀手亨利面对年轻的23岁克隆体小克,像极了导演李安的处境,“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我和自己打交道很久,宁愿作我自己。主体亨利和年轻版杀手小克像是“两生花”的人物结构,自己和克隆体如何相处与共存?如何达成和解?父权之下如何看待人性与自我认知?两个人都有自己的困局。但这些并没有使电影跳出题材的俗套,亨利的困局来自正义无关身份和人性的复杂,小克则受困于打破伦理,因此两人都不能随性做自我,只能违背本心。两个人的冲突无法避免,这样强烈的命运冲突反而让两人的友情更加可贵。

影片中,亨利是一名顶尖的职业杀手枪法神准。但正是因为杀人无数,也使他受职业所累无妻无子,不敢付出任何感情。他最恐惧的不是死亡而是自己,终于有一天他决定退休,却也因此被组织追杀。而那个让他陷入刀山火海的杀手,正是被改良的年轻的克隆体。人之所以为人,正是因为自身的人性情感,体现在片头亨利射杀高铁对象时险些失手。因为无辜女孩的干扰,他迟迟不愿扣下扳机。可以想见两个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一个为了退休,一个为了“克隆人之父”魏瑞思。印象最深的是,小克绝望而讽刺地大声质问亨利:“不做杀手,难道让我去做医生律师吗?”亨利坚定地回应:“不,是做一个丈夫,一个父亲,去做因为杀手这个职业,我从来都没有做过的事情。”

两人初见时互为恐惧都认为自己见到了鬼,他们能从彼此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也能体会到对方的孤独,能在世上遇到相知的人实属不易。片末,两人共同抵抗控制欲极强的“克隆人之父”魏瑞思,显得顺理成章。电影中老年与青年,似乎是李安从“儿子”视角转变成了“父亲”视角。亨利和克隆人小克的对话,俨然就像父与子的对话。最终,他和镜子中的自己和解,像极了希区柯克《迷魂记》的真假玛伦,基耶斯洛夫斯基《两生花》的薇罗尼卡,又像是张艺谋《影》的子虞和境州。但更重要的是,他代表着美国和中国文化之间的碰撞。

电影内核,依旧是李安擅长的俄狄浦斯情结下的父子伦理关系,也使得亨利的性格带着东方式的内敛与阴郁,但依然无法掩盖故事的单薄。
该片和《比利?林恩》一样,枪战动作场面较短,常规对白容易出戏。剧情拖沓和情节转折略显生硬,这些都导致该片在北美和中国的口碑遇冷,票房不甚理想。

科幻片影像远超电影内涵
今天的科幻就是明天的现实,许多科幻片远超电影本身的内涵,与人类历史、科技文明、未来生活紧密相连,具有惊世骇俗的视觉奇观。一百多年前《月球旅行记》人类带着魔幻色彩登上月球,这是人类探索宇宙具象化的预演;1997年科幻片《变种异煞》中的基因识别技术,为亲子鉴定、案件侦查和考古研究指明了方向;《银翼杀手》、《机械公敌》、《终结者》等仿生机器人如今已见雏形,人类甚至担心起“克隆人的进攻”;而在《双子杀手》中,没有恐惧、没有质疑、没有道德考量的克隆人,让我们站在了人类和未知世界的二元对立上。

因而科幻片在畅想未来生活时,有两种思潮。一种是未来可控的乌托邦式的幻想,正如《星球大战》和《星际旅行》系列等。而《双子杀手》代表是的,则是反乌托邦式的,科技发展使得人类无法掌控未来。这些负面性在人类自以为聪明的前提下毁灭了人类自身,正如《黑客帝国》、《终结者》、《银翼杀手》等,这些机器人拥有自我意识,甚至可怕到控制和奴役人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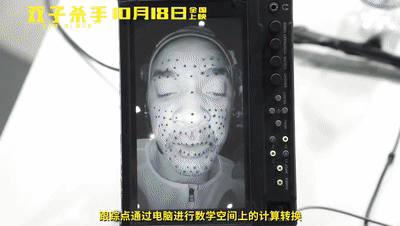
《双子杀手》中,亨利好不容易与克隆体小克化敌为友并肩作战,反杀“克隆人之父”魏瑞思,但一个更年轻的亨利克隆体出现在片末。针对人性的思考,内心的自我博弈成为科幻片表达的核心。《黑客帝国》等人类需要战胜自己创造出来的对手,《月球》人类需要战胜另外一种生命形态克隆人。这种伦理道德,使得“我”和诸多克隆的“我”之间难以厘清关系。《双子杀手》站在《银翼杀手》的层面,思考克隆人的完美和人类本身的缺陷。

记得《少年派》中李安提醒观众,帕克就是派的镜像,那是对生的欲望和对死的恐惧,而在《双子杀手》中亨利和克隆人小克也互为镜像,使得科幻电影超出了本身的内涵,学会放下,粉饰遗忘。可以说,科幻片表现的主题可以等同于批判精神的剧情片,观众可以悟出关于社会、家庭和伦理道德法律的思考,更能找到未来科技的归宿感。(影评原创,未经作者允许,私自将文章用于商业用途,一经发现一切法律后果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