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先洲散文两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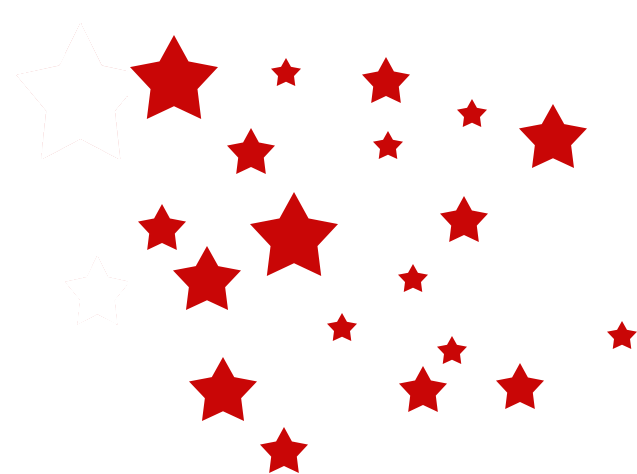
文/戴先洲(湖北)
1
鄢家拐
鄢家拐是村里的一块“飞地”,位于村东头小河对面。对岸的河坡地也属于村里。河堤以南就只有鄢家拐属于村里。小河是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人工开凿的,笔直的东西走向。原来有一条从西南方向蜿蜒而来的自然河被废弃了,变成了一段段水塘。人们叫它们老河。鄢家拐就是一块夹在新河与老河之间的三角形坡地,北靠新河的河堤,南临老河。这在风水学上谓之依山傍水、坐北朝南,绝佳的风水宝地。故而逐渐成为村里集中的墓葬地。
小时候鄢家拐就已有不少坟墓,但大都无人照管,风吹雨淋只剩一些小小的坟堆。高大一些的坟堆多半是我们家的,小时候每到除夕的下午,父亲就带我去鄢家拐给祖坟培土,铲掉坟上的杂草,再挑一些新土填上去,弥补坟墓一年的水土流失。尽管父亲每次都要给我讲哪座坟里埋着谁,但下次到墓地我依然分不清,那些躺在坟墓下的人我一个都没见过,我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否真实的存在过。只笼统的知道都是自家的祖宗吧。
我十四岁上初中,有一个学期走读,学校较远,每天天不亮就得出门,路上几乎不见人迹。而鄢家拐是必经之地。据说有坟墓的地方就会有鬼出没。所以每天凌晨经过鄢家拐时都会提心吊胆,生怕墓地那边忽然跑出一个鬼来,或者前方后方忽然有鬼出现。但我想起在这块墓地里我们家祖坟最多,应该有一定势力的,便在心里默默地祈祷,祖宗啊,我是你们的后代哦,每年都给你们烧过钱上过香的哦,你们别吓唬我,也别让其他的孤魂野鬼来吓唬我哈。我发现这种祈祷真会让自己安心不少,仿佛祖宗真的会保护自己。但无论如何至少一次都没见过鬼。有时会遇见附近村里赶早集的老头,老远我就紧张地注视着他一路走来,从我身边擦身而过。还有一次,远远地望见坟地里似乎有一团巨大的黑影,待到离近,才发现是有个老头在墓区放牛。一般人不敢去坟墓附近,故而墓区的草确实最为肥美。
待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父辈给每座坟墓都立了碑,我才确切地知道哪座坟下埋着谁,都有哪些祖宗长眠在那里。曾祖父、曾祖母、祖母、二祖父,这四位就是我小时候经常去祭拜、上初中走读时祈求保佑的,其中祖母去世最早,是在父亲不满周岁就病逝的,曾祖父母及二祖父逝于六十年代。八十年代中,和我们一起生活的二祖母也长眠在这里了,然后是九十年代末,祖父仙逝埋葬于此。然后是本世纪初祖父的幺弟弟媳即我们称呼幺爹幺婆的,也先后去世葬于此地,前几年伯母去世,月初一个堂叔去世,也都葬于此地。远房的以及村里其他人家的长辈这些年去世的也都葬于鄢家拐。村里熟悉的面孔越来越少了,而鄢家拐的坟墓越来越拥挤了。
鄢家拐不知何时在村里已成为死亡的代名词,成为村里人的最终归宿。好几年前,回老家时遇到村里的长者,问候身体怎么样,答曰就这样吧,活一天算一天,哪天不行了就搬到鄢家拐去住吧。村里李姓的玉品伯和远房的丑寅爹是邻居,老了常在一起拉家常。几年前,玉品伯去世,送葬那天,有个厨子和丑寅爹开玩笑,说玉品伯马上住到鄢家拐去了,您怎么不着急啊?丑寅爹淡定地说,不急,我胯子长,赶得上他的。玉品伯矮胖,丑寅爹高大腿长。厨子哈哈一笑回去忙锅里去了,不一会就听说隔壁丑寅爹走了,据说咳嗽了几声,一口气没上来就此断气了。
海涅说,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宇宙,每一块墓碑下面都埋藏着一整部世界史。每一个长眠在鄢家拐的人们又何尝不是一部世界史?
许多年里渐渐知悉了祖辈的一些事。曾祖父年轻时家境是不错的,后来战祸不断,家境日益衰落。曾祖父有四个儿子,老大吸大烟上瘾,后变卖田产准备远下南洋谋求出路,因故滞留于上海,盘缠花尽,死于上海,留下了一个遗腹女儿,这个女儿即我们的姑姑,后在上海成家,她的两个儿子生活都不错。曾祖父的二儿子即我前面提到过的二祖父,脾气暴躁,五十来岁就自尽,也只留下一个女儿,这个姑姑的后人也生活不错。老三老四即祖父和幺爹倒是开枝散叶,留下不少后人。
几年前在祖父的坟旁多了一个小小的坟堆,那是父辈为客死异乡的大祖父设的衣冠冢,其实衣冠也不可能有,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坟墓,但不妨碍我们每年虔诚地祭扫。
随着我们年岁渐长,我们也越来越感知祖辈的生活轨迹,感知他们每一段经历里的困惑与挣扎,那些墓碑下的人们越来越鲜活。鄢家拐也仿佛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那一年,我即将满二十九岁,在一家国企施工单位干着一份简单轻松的工作,收入也不错。但也仅止于此。从那些老员工身上,你能清晰地看见自己将如何变老,能看见自己如何度过一辈子。我不甘心就那么老去,希望自己能换一种活法,做些自己喜欢的事,不枉自己来人世走一遭。但这需要决心,需要面对未来的巨大不确定性。我把两年的年假攒在一起休,希望用足够的时间去寻找改变生活轨迹的契机。那一年我回到故乡,在一个午后去鄢家拐的墓区徘徊。是春末夏初时节,墓区还长着一些散落的油菜籽长出的瘦弱的野油菜,稀稀疏疏,开着残败的油菜花,阳光灿烂,照耀着那片三角形坡地。我忽然觉得鄢家拐很美,长眠在那里是一种福气。我对自己说,我从此就当过去的自己已经死去,并且埋葬在了鄢家拐,今后的我将是一个新生的我,一个不受过去的经验和价值观影响的我。从那以后,我的人生真的就经历了天翻地覆的改变。而今二十余年过去,我已年过半百。经历过走投无路,也经历过大起大落,经历过价值观的毁灭与重建。生活远比在单位时艰辛,但也远比在单位自由和刺激。成败并非最重要的事。最重要的是,只有真正投入地生活过,才可以安宁地面对人生的终点。
而今想起鄢家拐时,我也会常常想起二十余年前的那个午后。鄢家拐,总能让我们直面生死,直面生活的真相,如同我们人生的课堂。我也会偶尔想起上初中时那个在墓地放牛的老头,那时非常佩服他的无所畏惧。现在想,一个人活到老了,该经历多少比死亡更可怕的事,墓地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1
棉花
在网上看篇文,文中提到有人曾写过一句诗:白云白啊,像棉花一样白。一下子勾起了关于棉花的记忆,眼前仿佛浮现出一望无际的棉田,烈日当空,无数朵白灿灿的棉花在棉叶间闪闪烁烁。
故乡是湖北天门,原是人口大县,后改为市。上世纪八十年代,天门曾以“三花”闻名全国。一是状元花,恢复高考后天门每年有上千人考上大学,为全国之冠;二是塑料花,据说中南海的花瓶里,插的都是天门塑料花厂的产品;第三就是棉花,年产万担棉,是主要的产棉大县之一。“三花”是否真的这么牛皮,我其实并不知道。我只知道,八十年代很多大学毕业的天门籍穷学生,就是靠吹这个牛皮,把城里女孩忽悠得一愣一愣的,用一双捡过无数棉花的手,成功抱得美人归。
很多年,故乡的主要农作物都是水稻麦子和棉花,种麦子和种棉花是同一块地,麦子收完种棉花,棉花收完再种麦子。“高田里种芝麻,矮田里种棉花,棉花田里一窝蛋,捡底回去姆妈看。”这首天门儿歌里说的矮田里,只是相对于芝麻田。比起水稻田,棉花田一般在地势略高处,也可以称为“高田”了。正规点的划分是把农田分为旱田和水田。
清明前后播种,六七月份开花,结出小小的棉桃,八月份就开始有棉桃裂开,绽出白白的棉花,通常说的棉花并非棉的花,而是棉的果实。棉桃裂开到最大,棉花变得蓬松而洁白,确实有如一朵洁白的花。这时就要开始捡棉花了,把棉花从裂开的棉桃里揪出来,就叫捡棉花。大概要到十月底、十一月初才能捡完。种棉花需要很多劳作过程,比如做营养钵、点棉籽、施肥锄草、打农药、打顶心、捉虫子、插杨枝靶抓蛾子等,最后也最重要的是捡棉花。捡棉花也不算最后的事,最后应该是拔棉梗、捆好、挑回家。如此,地里一年的棉事方才算完全结束。
除了打农药,其它所有的劳作过程我都参与过,干的最多的是捡棉花。这些过程若是一一展开,写起来会没完没了。先简单说说打顶心、捉虫子、插杨枝靶的事吧。
打顶心又叫掐顶心。棉树并非长得越高大越好,太高太大反而不结棉桃。所以长到一定高度,就要把棉树的顶尖掐掉,限制它长高。某一年剁资尾,屋后的竹林和树林大部分都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剁掉了,后来这块地被当成了棉花试验田,全部用营养钵播种,肥料充足,根红苗壮,棉树长得粗壮高大枝繁叶茂,高过了成人的头顶,只是结的棉桃却少得可怜,而且由于棉叶过于肥大,棉桃得不到充足的日照,多半都烂掉了。因这块棉田就在屋后,孩子们经常去田里捉迷藏扮家家。也常有鸡去觅食和乘凉,在这块棉花田里捡到蛋很寻常。这块试验田用铁的事实告诉人们,及时掐顶心多么有必要!
有一年夏天,每天一大早就拿个玻璃瓶去棉花地里捉虫子。有些虫子就在外面爬动,一眼可见,有些则要仔细观察每朵花、每个棉桃,有新鲜虫眼的棉桃,掰开后基本都能找到一条肥肥的虫子,把这些虫子揪出来装进玻璃瓶,拿回去交给生产队的会计,会计会用竹签扒开来数出条数,记录在册,按规定换算成工分。因此那些恶心的虫子在我们眼里都格外可爱,捉到越多越开心。
杨枝靶不知是从何处普及而来的,不大可能是天门人的发明。如果是天门人的发明,更应该叫柳枝靶的。因为全国似乎只有天门把杨树叫柳树,把柳树叫杨树。做杨枝靶用的树枝都是从天门人称为柳树的树上砍下来的,本文里也与全国人民一起叫它杨树吧。砍一些杨树枝,把树叶丰富的树枝的末梢,截成一尺来长,扎成一把一把的,就是一个一个杨枝靶了,再树叶朝下插在木棍上端,像给棍子戴了一个帽子或者一副假发。把木棍的下端插到棉田里,木棍的长度要使杨枝靶至少能高出棉树,要足够醒目方便蛾子看见。傍晚时蛾子们会飞到杨枝靶上钻进树叶间过夜,取下杨枝靶在蛇皮袋里抖一抖,就会扑愣愣地飞出许多蛾子,在蛇皮袋里乱飞乱撞,这时要马上取出杨枝靶,收紧袋口,拍晕这些蛾子,以免它们又飞走了。收完蛾子后的杨枝靶再重新戴上木桩,最多重复使用两三天,树叶就干枯稀少了,每天都要做一些杨枝靶用于更新。
隔一段距离就要插一个杨枝靶,所以需要砍很多杨树枝,做很多杨枝靶。这活本和我无关的,但那年大哥考上高中,却被大队书记以家庭成分不好为由强行剥夺了入学资格,到生产队上工,就负责杨枝靶这件事。我则被他拉着当了他的助手。那一年他十三四岁,我九岁。我看着他爬上一棵杨树,一手抱着树干,一手握住篾刀用力砍向一根杨树枝,忽然大叫一声从树上掉了下来。厚重的篾刀脱手掉下,正好砍在了脚踝处。流了很多血,但幸无大碍,“轻伤不下火线”,第二天又带着我收杨枝靶了。收杨枝靶要在黄昏天色擦黑时,棉花田里几乎已无人影,我是不愿意去的。大哥便跟我谈条件:去了给你一分钱!我说不行,要给两分钱才去!大哥大约是捡知了壳或是剥构树皮卖了一些钱,兜里颇有几毛私房钱,倒也痛快:两分就两分,现在就给你!我便揣着两枚硬币,兴高采烈地跟着他,向远处暮色笼罩的棉田走去。其实我去了也就是帮他牵一下蛇皮袋,没我他自己也能做到的,他之所以一定拉我去主要是给他做伴壮胆,他怕棉花田里闹鬼。村东头余家桥的春安姐,听说有个傍晚就被鬼下了迷魂罩子,被罩在棉田里原地打转,始终走不出来,后来还是她家里人听到哭喊声把她接出来了。这事全村都知道,所以棉田里闹鬼绝对不只是传说。我当然也怕鬼,可是和大哥在一起就觉得无所畏惧。在我眼里他就是个大人,无所不能。其实他虽然大我四五岁,那时也不过是个十三四岁的孩子。他内心的恐惧恐怕还远远多于我的。四年后,他成为一所中学的高考状元,也成为恢复高考后生产大队考上大学的第一人。
捉虫子和插杨枝靶在实行包产到户后,都不用干了。人们发现只要农药打得认真细致点,压根就不该有那么多的虫子和蛾子。集体时打农药太过糊弄了,要么农药加的少,要么很多地方根本没打到,甚至有人背着空药桶假模假式走一圈,就算打过农药了。大锅饭才是真正的幺蛾子!
棉花地太多,全靠人工一朵一朵去捡。高峰期里光靠主劳力是忙不过来的,就会让老人小孩齐上阵。我刚上小学时学校就经常组织劳动,全校师生一起出动,排着长长的队伍,浩浩荡荡,开拔到某个生产队捡棉花。劳动结束还会有圆珠笔和算术本之类的小礼品可领。
没两年便包产到户了。要捡自家的棉花。每天放学到家后取出书本,背着空书包去地里捡棉花。捡满一书包,去倒进田头的斤篮里,再去接着捡。斤篮是用竹片编的网格状大圆框,直径和高度都约摸一米,专门用于装棉花的。包产到户后,棉花的亩产量何止翻番,更是捡不赢。大人们就在白天连棉花撮子一起囫囵揪回家,晚上一家人再慢慢掰弄。棉桃裂开,外壳会逐渐失去水分,变得枯硬,这就是棉花撮子,撮子的尖端更是坚硬如刺,很容易伤手。晚饭后收拾好桌子,在桌上放个大簸箕,父母把带着棉花撮子的棉花堆在簸箕上,堆得像座小山,一家人就围着这座小山开始劳动,把棉花揪出来,把棉花上粘的叶屑清理掉,一个一个,一遍一遍,机械地重复着同样的动作,小山渐渐变得低矮直至消失,父母就再堆上新的小山。如此循环往复,没完没了,仿佛永远没有尽头。一直干到夜深,哈欠连天,父母便叫我们先去睡了,第二天好上学,他们继续把剩下的都掰完。至于他们是干到鸡鸣还是通宵达旦,我一概不知。第二天醒来,棉花是棉花,撮子是撮子,都晒在屋外了。父母早已去田里,开始了新的一天忙碌。
偶尔也会有惊喜,有次正在大家昏昏欲睡的时候,父亲忽然起身,从房间的柜子里神神秘秘地拿出一捧花生,每个孩子分一小把。香喷喷的花生立刻让我们精神大振,赶紧剥开一个,将花生米放进嘴里细细咀嚼,满口生香啊!可惜一小把花生很快就吃完了。余味无穷,完全不过瘾。就像一场好戏刚刚开锣便已结束。大家便把掉落的花生皮屑收集起来,继续品味。大哥甚至把花生壳都放进嘴里嚼着聊以解馋。这些花生是住在汉江附近的姑妈给的,她们那儿沙土多,适合种花生,父亲每次去姑妈家,口袋里都是鼓囊囊的装着花生回来的。所以每次父亲从姑妈家回来,我们都两眼放光地盯着他的口袋看。但这次的花生是什么时候拿回来的,我们谁都不知道。不然父亲藏得再好也会被我们翻出来的。
这样的日子随着我们陆续去外地中学住读渐渐少了。家里的农活除了暑假我们会参加双抢,几乎都是父母和已经退学的姐姐包了。经常周末回家,天都黑了,父母和姐姐仍在地里忙碌,迟迟未归。
收好的棉花每天要搬出去晾晒,晒干后用板车拉到采购站去卖。一个乡只有一家采购站,站前每天都排着几公里的长队。十里八村的农民们守着自家的板车,在炎炎烈日下一等就是大半天。卖棉的队伍有时缓缓移动,有时好久不动。有些和采购站工作人员有关系的农民是无需受排队之苦的,和熟人打个招呼直接就拉进去了,还能定个好级别,卖个好价钱。大部分老实巴交没有关系的农民只有老老实实地排队,忍饥挨饿,忍受着内心的焦灼与忐忑不安,也忍受着毫无遮拦的烈日的暴晒。这种局面直到后来国家取消了统购统销的政策、放开了棉花市场,方才结束。采购站从此也由门庭若市很快变得门可罗雀,直至完全废弃。
种棉苦,卖棉更苦。但那些年棉花一直是农民们的主要经济来源。八十年代搞新农村建设,人们盖新房、买电视、买自行车,都是棉花的功劳。父亲有五个子女,除了姐姐早早辍学外,其余四个一直坚持读书直至读完大学。每到开学前夕,父亲就四处借债为我们筹集学费,给人家的承诺就是下季卖了棉花马上就还。父亲深谙有借有还再借不难的道理,每次都会说到做到。在天门,无数家庭也是靠棉花供孩子完成学业,考取大学。可以说先有棉花,才会有状元花。棉花提供了上学所需的经济保障,而种棉的辛苦,又何尝不是无数天门学子奋发学习的一种激励?许多年后,这些学子们大都成为了各条战线各个行业的中流砥柱,用他们捡过无数棉花的手,指点江山,激扬文采。例如国家发改委原副秘书长范恒山、两会新闻发言人张业遂,都是出自天门农村普通贫寒的农民家庭。
而今的江汉平原,很难看到棉花了。一是棉花的价格长期低迷,种棉得不偿失;二是农村劳动力太少,也实在应付不了种棉所需的繁重劳动。现在的农田已没了旱田与水田之分,一马平川的江汉平原,“旱田”与“水田”、“高田”与“矮田”,区别原本不大。除了少量的黄豆芝麻之类杂粮,绝大部分田都用来种麦子和水稻。收了麦子种水稻,收了水稻再种麦子,基本都是机械化作业。收割完了甚至有人直接去田里收购。种田的收入微薄,但种田的辛苦的确成为历史了。几十年来,中国逐渐完成了工业化进程,绝大部分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早已不是农业,而是依靠在城里经商打工等。
“白云白啊,像棉花一样白”,也许不是一句好诗,却轻易唤醒了我许多关于棉花的回忆。我猜想诗人或许和我一样,也有着深深的棉花情结。对于每一个在棉农家庭长大的人而言,棉花不仅仅是棉花,同时也是苦难、沉重和希望……
作者简介

戴先洲:笔名江南秋叶,年方知命。生于湖北,求学沈阳。谋生白山,后下沿海。做过工程,干过编辑。孤身打拼,多逢贵人。历经沧桑,始知感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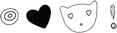

![]()


《武汉文学》(季刊)是由武汉市文联主管,武汉散文学会主办的大型文学期刊。一贯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办刊理念;坚持精品战略,重点推出具有强烈时代感和高度艺术性的精品力作。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和省第十次文代会、第七次作代会精神,充分展示新时代文学艺术的新魅力,进一步扩大《武汉文学》的影响力,努力将其打造成为中国知名优秀文学刊物之一,更好地为广大文学艺术爱好者提供交流和学习的平台,经武汉散文学会及《武汉文学》编委会研究决定,面向社会长期征集文学艺术作品。

![]()
组织机构

主办
武汉散文学会
承办
《武汉文学》公众号(微刊)
《武汉文学》(季刊)

![]()
征集内容

凡是与文学艺术相关的散文(优先)、诗歌等不同体裁作品均在征稿之列。

![]()
投稿要求及说明

1、文学作品体裁、字数不限,要求立意新颖、内容充实、文笔清新、简洁流畅,兼具思想性和可读性;
2、书法作品书体不限,但草书、篆书须附释文;
3、绘画、摄影作品体裁及种类均不限。摄影作品须为不小于3M的JPG格式电子文件,传统照片须扫描为同规格的数码照片;
4、投稿时注明“投稿《武汉文学》”字样,不要附件发送,可直接粘贴在邮件内,并提供真实姓名、详细联系地址、电话、邮政编码、微信号等通联方式,生活照1-2张。否则,将视为无效投稿;
5、所有投稿必须为原创作品(拒绝在其他公众号推出的作品,如发现则拉入黑名单),更不得有侵权行为。否则,相关法律责任由作者承担,《武汉文学》(季刊)不负任何连带责任;
6、鼓励投稿作者“一月一投”,超过一个月没有收到拟用或是刊用通知的,作品可另投;
7、所有来稿一律不替保存,请自留原稿;
8、《武汉文学》(季刊)编辑部负责解释征稿相关事宜。

![]()
作品发表说明

1、优秀作品先于《武汉文学》公众号(微刊)推出(如不同意公众号推出,投稿时请注明);
2、《武汉文学》(季刊)将从公众号(微刊)优选作品予以发表;
3、《武汉文学》(季刊)选用作品作者,将获赠当期刊物一册,如另有需要可与编辑部联系;
4、《武汉文学》公众号微刊编辑制作时所选图片均来源于网络,如涉侵权,请联系删除;
5、在《武汉文学》(季刊)发表过散文作品的作者,可优先吸收为“武汉散文学会”会员。

![]()
投稿方式

邮箱
wuhanwenxue@sina.com
(请尽量邮箱投稿)
微信
Wm475553460
lyf354583777

武汉散文学会
《武汉文学》编辑部
2018年5月20日
